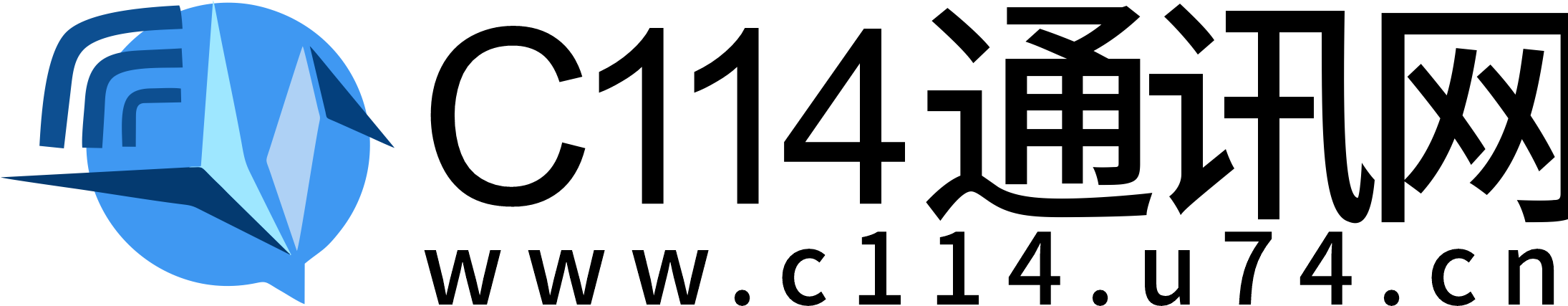巴尔扎克的“幽灵”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读李亚《巴尔扎克的银子》
文/马兵
“……所有人都看到我舅舅和我舅妈不得不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就像捏着一只萤火虫一样,向更深更远更加光怪陆离的庭院深处走去。”在定格下舅舅和舅妈微光中并排的身影后,《巴尔扎克的银子》戛然而止了,读者终于能从舅舅对巴尔扎克各种琐事充满自矜的讲述中,从作为外甥的叙述者混不吝而又遍布细节的絮叨中缓口气,不过一串疑问随之而来,小说真的结束了吗?进入庭院的舅舅和舅妈会邂逅什么,大牛在谯城七十二号摆下的宴席又将上演什么荒诞或精彩的戏码?毕竟,在结尾之前,小说里任何伸出主干的枝蔓都被活色生香地描写或调侃了一番:户籍警马茂谡对二夹弦的热爱,舅妈唱《秦雪梅吊孝》时那“异常悲凉的穿透力”,文化馆里令人啼笑皆非的讲座,对太平天国如数家珍的牛羊肉专柜的售货员齐姜大嫂,暴发户大舅方全,还有“我”那个在国外放浪不羁的表弟老九……在舅舅和舅妈结婚与离婚这一家庭事件的串联之下,无数故事和嬉笑被吸附进来,大大加强了小说的密度,让人觉得它似乎可以无限膨胀下去,构成一部小城版的“人间喜剧”。而这“无节制的野心”也正是巴尔扎克曾展示出来的,李亚这篇颇见学识的小说不但频频借舅舅之口,建立文本与巴尔扎克作品和传记资料的对应性,还用泥沙俱下的芜杂、持续茂长的情节、对人的生命活力与隐微人性的洞察来致敬巴尔扎克。
波德莱尔在1859年写成的《论泰奥菲尔·戈蒂耶》(戈蒂耶也是小说里被舅舅反复挂在嘴边的人物)中,谈到巴尔扎克时,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一直以为他最主要的优点是:他是一位洞察者,一位充满激情的洞察者。他的所有人物都具有那种激励着他本人的生命活力,他的所有故事都深深地染上了梦幻的色彩。与真实世界的戏剧向我们展示的相比,他的《人间喜剧》中的所有演员,从处在高峰的贵族到居于底层的平民,在生活中都更顽强,在斗争中都更积极和更狡猾,在苦难中都更耐心,在享乐中都更贪婪,在牺牲精神方面都更彻底。总之,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每个人,甚至看门人,都是一个天才。所有的灵魂都是充满了意志的武器。这正是巴尔扎克本人。”用这段话观照《巴尔扎克的银子》,我们会发现无论舅舅、舅妈,还是齐姜、大牛、方全、老九,小说里出场的各色人等也都具有无比热辣的生命活力和某一方面的顽强,他们以肉身深入世俗的泥淖,荤腥无忌,一举一动皆有一种表演性,而也正因此,他们得以与被庸常磨蚀的众人区分开来,不但自己活成广阔生活舞台的主角,“就像泥鳅一样扭来扭去窜来窜去”,还带来一种“梦幻的色彩”,散发着由怪异的性格力量和热情的“意志”所激发的独特气质,从而令读者过目难忘。
以小说的主角舅舅方程先生而论,这个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痴迷于巴尔扎克,致力于写成比《人间喜剧》还要浩繁的研究巴尔扎克的巨著。他凡事比附巴尔扎克,认为巴尔扎克结婚花了十八年,自己的离婚拖拖拉拉七八年再正常不过;他津津乐道于巴尔扎克和其他法国作家的艳情秘史,自己在生活中也毫不收敛对各类女性的欲望;一方面他随性无比,几杯下肚就和外甥称兄道弟;另一方面,在事关巴尔扎克的文学理解上,又丝毫不肯让步,比如他坚持认为《驴皮记》才是“巴尔扎克写作风格和文学品质走向成熟的转型之作”,“这本书的诞生直接将巴尔扎克推向了这个狂妄胖子早就大流涎水的大师行列”。舅舅与舅妈的相处也是如此,无论是每次看舅妈演戏必坐在最佳位置等谢幕后再持花献佳人,还是夫妻冲突时让舅妈抓挠得遍体鳞伤,抑或结尾处被舅妈翘着兰花指、踏着莲花步的身影打动而要同她重归于好,舅舅在爱情和婚姻里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是为印证巴尔扎克那句名言——“热情就是整个人类”!
从不按套路出牌的舅舅和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巴尔扎克,在小说里结为一种彼此塑造的镜像关系,而作者对巴尔扎克的作品以及关于他各种正史和野史的谙熟,让小说的叙事者得以语俚而意切地“编制”他们“恶习和德行的清册”“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换言之,《巴尔扎克的银子》采用了一种激进也相当有趣的互文性写作策略,它不但吸收和转化了巴尔扎克的诸多小说与传记资料,诸如《幻灭》《贝姨》《驴皮记》等名篇,乔治·桑的《我毕生的故事》、安德烈·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戈蒂耶的《浪漫主义回忆》、福楼拜的《福楼拜文学书简》,电影《巴尔扎克激情的一生》等,还让舅舅以实践的方式重演巴尔扎克现实人生和作品世界的分裂和纷乱,甚至在叙事中有意模糊两者的身份,把舅舅的研究、写作与巴尔扎克的悲催人生并置,比如小说有一节这样写道:“乔治·桑肥胖的身躯导致嗓门粗哑,震得我舅舅心惊肉跳,更不必说眼看着桑多用委婉的眼神央求乔治·桑道,好心肝儿快点闪了。我舅舅为了留住乔治·桑欣赏他刚写的情节,不得不友好地对桑多说:小朋友,咱们还是先从梦幻般的骚味中醒过来吧,尽快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们首先谈一谈欧也妮·葛朗台这个人物。”此处,舅舅以无比的真诚“戏仿”巴尔扎克的人生,甚至将自己同巴尔扎克无缝置换,这把他言必称巴尔扎克的痴态描写得活灵活现,制造了令人捧腹也促人省思的艺术效果。
在有力地塑造人物形象之外,舅舅与巴尔扎克身份的互文,还赋予小说叙事内在的开阔。小说中关于巴尔扎克的逸闻趣事,大多借舅舅之口道出,但有时则有意省略或延宕出处,以直接插入的方式制造“侵入式叙事”的效果,比如“一八五零年八月十八日是个星期天,深夜十一点三十分,巴尔扎克离开了既是他生活的那个世界也是他创造的这个世界。众所周知,在韩斯卡夫人代笔写给老伙计戈蒂耶的那封信的末尾,巴尔扎克写下了人生在世的最后一行字:我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巴尔扎克的幽灵既是舅舅也是小说的核心所系,而这个幽灵性的存在具有强大的派生能力,从老到少,不断娩出非常的人物,从情境到结构,持续产生反讽的力量,各种引用、掌故、模仿、交叉、增殖、扭曲等互文性的操作,充分打开了小说的叙事边界,让舅舅和舅妈狗血又拉杂的离婚闹剧成为巴尔扎克人生与作品巨大反差的一个今日注脚。不妨这样说,小说真正的线索不是舅舅和舅妈反复的离合,而是舅舅不断探寻巴尔扎克小说和人生的历程,它甚至具有一种元小说的意味,巴尔扎克的幽灵部分不但呈现了作者写作的观念,也告诉读者舅舅何以成为意志的强者和生活的病人,为读者提供了解释他一切乖张行径的依据。也因此,笔者以为,在嬉笑与张狂之下,小说对于巴尔扎克和他的幽灵也即舅舅,还有内在的哀矜和严肃的另一面。
让我们回到小说的题目上来,“巴尔扎克的银子”当然照应了巴尔扎克的金钱观和他那些攫取财富的失败投资,比如小说后半部分提到的,巴尔扎克想要在撒丁岛挖掘银矿却被奸商别兹捷足先登的逸事。梦想发财的巴尔扎克一生潦倒,数次破产,而窘迫于资财匮乏的噬心体验,却意外成为这个文学天才的晋身之阶,锤炼出他那勇于搏斗生活的“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最富有诗意的”一面,成就了卷帙浩繁的风俗史巨著。虽然在叙事者的转述和自述中,不断用“骚胖子”“鲁莽的胖子”之类的话来指称巴尔扎克,但一旦涉及巴尔扎克的文学世界,舅舅的那些话语就不再是戏谑之言,而是精细到别致的艺术判断,比如“纵观《人间喜剧》,我们可以看出巴尔扎克精通世间各种事物,甚至娴熟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而且他在作品中写的判决书与账单就像现实生活中专业人士写的一样毫无瑕疵;另一方面,巴尔扎克对各类人心洞若观火,所以他能够对人性的解剖宛如庖丁解牛明察秋毫”,这几乎是可以写入文学史的话。而作为巴尔扎克幽灵的舅舅既继承他强旺的生命意志、混乱的生活关系,也继承了他开阔的文学品格和精神。换言之,“巴尔扎克的银子”既是舅舅展示蓬勃情欲的“负面”资产,也是他力图捍卫的文学遗产。在别人看来只会夸夸其谈的舅舅,却身体力行地靠近偶像,全身心投入,他那些拒绝流俗规制的言行是颇让人产生几分敬意的。舅舅每一次对巴尔扎克的解说都积累着相当的叙事能量,不断让自己污名,也不断给自己正名。
最后想说说叙述者,对于李亚这样极富经验的写作者而言,选择什么人、从什么视角来叙述、借什么由头切入故事自然是他经过了反复思量的。这个小说由声称自己“不学无术”的药贩子外甥来述说,却忠实记录下舅舅对巴尔扎克所有的肺腑之言和精彩发见,而且他还曾用华丽铺排的比喻形容舅妈悲剧唱腔的穿透力“就像一把冰凉的利刃缓缓划开皮肤后执着而有力地直刺心脏,就像天河彼岸的七仙女泪流满面悲切切呼唤担着一双儿女的牛郎董永,就像希腊神话里那个人首鸟身的塞壬在暗夜里孤寂的大海上歌唱低迷的歌曲,那种天籁般的声音有着强烈的但凡活人都难以抵抗的类似极端妩媚一样的悲伤”,虽说他自谦这是来自舅舅的熏陶,却足见这个“不学无术”的外甥是颇有几把刷子的,而他那种汩汩俱来的叙述腔调和粗鄙的口吻,和巴尔扎克一起参与了对舅舅怪诞夸张的形象塑造。前不久辞世的翻译家郭宏安 先生曾谈到过,法国文学圈有一个关于巴尔扎克的“著名难题”,即巴尔扎克的文体,从他置身的时代一直到后世,不断有人批评巴尔扎克“写得不好”,指责他“文笔粗糙”“叙事拖拉”“描写臃肿”“不尚剪裁”等,对此,郭宏安引用阿尔贝·贝甘的话——“巴尔扎克,其学习是匆忙的,不受古典的匀称的影响……他不追求‘美的风格’的和谐,也不受‘崇高’的篇章的诱惑,如果那样的话,他肯定会跌进晦涩难懂和虚伪的高贵的泥坑。但是,他跟随他的最好的灵感,屈从而不是制造语言的暗示,根据叙事的变化选择他的表现”——指出,我们不能用美、均衡、适度和崇高等来评价巴尔扎克,而“繁复、芜杂、沉重等正是巴尔扎克的风格的力量所在”。我以为,小说蓄意采用粗鄙的腔调,还包括细节上的放纵,话语的狂欢,极尽调侃一切的姿态大约也与此相关,李亚把评论界指责巴尔扎克的那些缺点都拿来呈现为小说的风格,似乎在咄咄逼人地说:快别矫情了,在人间喜剧的舞台上,谁又能抽身事外呢!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